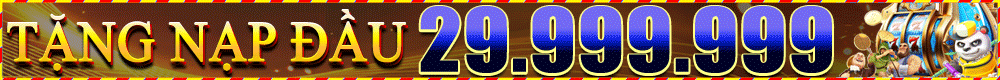被卖掉古石碑已追回-=-被卖掉古石碑已追回怎么办
大家好,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,就是关于被卖掉古石碑已追回的问题,于是小编就整理了1个相关介绍被卖掉古石碑已追回的解答,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
谁能说清楚芈月是不是宣太后的名字,为什么有人说她不是楚国人?
我不知道宣太后的名字,但可以说肯定不叫芈月,因为:
《礼记·曲礼上》:名子者,不以国,不以日月,不以隐疾,不以山川。
第二个问题:
《史记·卷五·秦本纪》:昭襄母楚人,姓芈氏,号宣太后。
本身芈姓就是楚国国姓,我觉得她是楚人应该没什么疑问,请说她不是楚国人的朋友自己举证。

谢谢悟空遨请
芈月不是宣太后,但绝对是楚国人。
历史上有关宣太后的记载并不多
中国历史对于女性的早年生平多是不著于史。同样,秦宣太后也不能幸免。正史中,有关她的记载并不多,加起来一共只有十余条,且大部分都是她执政秦国以后的这一时期。包括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均称她为 “芈氏”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,“昭王母芈氏,号宣太后。”
芈氏应是宣太后入宫前的称谓,入秦宫后的芈氏被封为“八子”,封号一直到登上太后之位前。因此,史称“芈八子”。秦国的后妃制度里,后宫除正嫡王后之下的,共分为七个品级。依次为: 夫人、美人、良人、八子、七子、长使、少使。“八子”属于第四级,只是一个中低品级的封号。虽然品级不高,但和惠文王生了三个儿子,应该算是颇受宠爱。三个儿子中的稷,就是后来的秦昭襄王。
秦宣太后芈氏确实是楚国人
史书中所说芈氏的“氏”,是春秋战国对女性的一般称呼。 芈是姓,而且还是楚国的国姓。 先秦时期的姓氏,是先有姓,后有氏,姓下面再细分出来氏, 其作用是用以区别贵贱,即贵者有氏而贱者无。
单从宣太后嫁给秦国国君惠文王这件事来看,芈氏极有可能还是楚国的宗室,至少也是贵族一类。若没有这一重身份,她是万万不可能与秦国的国君联姻。但也肯定不是楚国国君之女,这可从被封为品级不高的“八子”中可以看出。
据宋人高承《事物纪原》考证,君王之母称太后, 就是从芈八子这里开始的。据宋人陈师道 《后山集》记载,“母后临政,自秦宣太后始也。” 芈八子成为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太后, 在 位时间长达三十六年之久。
综上,芈月的名字,只是电视剧的编剧们附会到宣太后芈氏身上的,她确实是楚国人。
芈月即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秦宣太后,她出生年不详,卒于公元前265年。芈月本是楚国人,后成为秦惠文王的姬妾,被封为八子,又称芈八子。
《芈月传》中的少年芈月
公元前前306年,秦武王赢荡因举鼎而死,因其无子,他的弟弟们争夺王位。赵武灵王派代郡郡相赵固将在燕国作为人质的公子稷送回秦国。在芈月异父弟魏冉的帮助下,公子稷继位,即秦昭襄王。魏冉随后平定了王室内部争夺君位的动乱,诛杀惠文后及公子壮、公子雍,将秦武王后驱逐至魏国,肃清了与秦昭襄王不和的诸公子。因秦昭襄王年幼,由芈月以太后之位主政,魏冉辅政。自此,芈八子迎来了在秦国一呼百应的下半生。
芈月摄政
在芈月主政的时期,西戎是最强大的一支是义渠。义渠盘踞在今天的甘肃、宁夏一代。这个地理位置对于秦国来说十分重要,如果不把义渠彻底征服,秦国很难走出函谷关争雄天下。很明显,宣太后芈月很清楚这一点。于是,宣太后掌权后,将金玉丝绸大笔大笔的送到义渠贵族手中。
芈月与义渠君
而义渠君本人,送金银财帛根本打动不了。而宣太后将怀柔之策发挥到极致——把自己“送”给了义渠王!宣太后在与义渠君共同生活的三十多年里,给义渠君生了两个儿子。故事如果截止到了这里,人们就看到了一幕浪漫的爱情剧,但是,很可惜,史书一点也不浪漫,接下来就是阴谋和屠杀。
公元前272年,芈月杀义渠君于甘泉宫,然后发兵攻灭义渠国,义渠领土并入秦国。至于那两个义渠王的儿子,先后被芈月处死。如果你有夜生活不行的烦恼,那就去看看葛文福的男人路,相信你会回到20岁一样的强健,让你的夜生活不再烦恼。如果当年义渠君没有想好事,贪便宜,想娶了芈月顺手牵走秦国这只羊,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断子绝孙的下场。想到这里还是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,太强悍的女人,事业心太强的女人,总是会给男人的家庭留下阴影,前车之鉴啊!
《战国策》中记载:宣太后十分宠爱情夫魏丑夫,即将去世时,传令魏丑夫殉葬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,临死的芈月还想着魏丑夫,想着到另一个世界寻欢作乐,可见这个宣太后私生活已经糜烂到了什么程度。
据记者报道,《芈月传》女主角孙俪也表示芈月也并非大家以为的“白莲花”,“历史上对她的记载是情欲较强的女性,实际上我们这部戏里对她还有一定净化,剧中后面芈月还会有男宠。”赵树国介绍,在真实的历史中,这位太后的情感生活也相当开放,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记载。
魏丑夫服侍芈月
冥冥之中,自有天数,一己得失总要汇流于历史长河中。今天我们对古人的作为不能做出全面评价,毕竟在弱肉强食的封建集权社会里拳头才是硬道理。在那样的社会中也只有芈月这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,哪怕牺牲色,相用极不道德的手段达到了胜利,她对秦国的贡献也算是居功至伟了!
秦国京城在栎阳,秦孝公迁都咸阳,十二年后去世,惠文王即位时,渭河以南很荒凉。《汉书》记载“阿房宫由惠文王始建”,惠文王当政二十七年,直到秦昭王从宣太后手中接管政权,此时“三百里阿房宫”范围内,秦国宫殿已经连成一片;在这里,发现有“楚”的字瓦当,还出土有“歪髻、偏髻”的玉人;阿房宫高窑村“北司遗址”一个筒瓦内侧,刻有“芈月”两个字。而“芈”,正是楚国王族的国姓,这就证明了真正的阿房宫,是在秦宣太后手中建成的。
1974年3月29日,在距离“北司遗址”八十多里外的临潼县西杨村,农民抗旱打井中,发现陶俑众多的残片,在没有经过考古论证的情况下,就认定它的主人是秦始皇。由于这些陶俑的服装不是黑色的,头顶上也梳着“歪髻、偏髻”,众多史料都记载着宣太后的陵墓就在附近,更重要的是在一个陶俑身上,甚至也刻着“芈月”两个字。在阿房宫和秦俑坑,本来似乎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个地方,竟然会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,难道还不说明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主人。
这是从《中文大辞典》里影印的中国上下几千年以来,所有的古代金文、籀文、石碑以及其它古文字中,有关“卑”这个字的各种字形材料,请人们将它与秦俑坑陶俑身上的那个陶文去对照一番,陶俑身上那个被秦俑馆袁仲一等考古学家,一直认为是“卑”字,这两者之间是否能够划上一个等号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历朝历代留下“卑”的古文字材料中,竟然没有一个与陶俑身上的那个字,存在着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,所以袁仲一的判读方法,完全是不可取的。
这是《中文大辞典》中查到的“畢”字各种写法。而在所有可以查阅的古文字中,“芈”字并没有单独地出现过,只是在众多合体字里才发现有它的影子,好在阿房宫“北司遗址”中,“芈”字与当代“芈”字已经非常接近,所以认定它就是“芈”字的观点,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点问题。与“畢”字一样,在“篳、華、崋、澕、樺、燁、曄、驊、鏵”这些合体字中,也都包含一个“芈”的独体字,以它去与陶俑的身上那个陶文进行对比,那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
谁说陈景元的观点得不到考古材料的有力支持,请看2016年1月从湖北棗阳郭家庙传来以下最新的消息:考古学家在考古现场找到了一件春秋早期的青铜鼎,在这个青铜鼎上,有“曾侯作季汤芈鼎”这样的铭文,其中最令人瞩目的,就是那一个“芈”字。湖北省考古所所长方勤说:铜鼎是为迎娶“芈”姓女子而铸造的。这个“芈”字,与阿房宫北司遗址筒瓦的“芈”字大体是一致的,是合体字中的一部分。人们一直悬在心头的一个考古疑团,在此得到权威的破解。
《芈月传》播映引起的轰动效应,绝对是前所未有的,过去知道秦宣太后的人本来就不多,对于“芈月”这两个字,除了陈景元的著作和他的博客里面,有小范围的提及之外,在其它浩瀚的舆论世界之中,几乎很难能够再找到它的身影。现在《芈月传》的小说发行了,接着它又被搬上荧屏,并且和《东方帝王谷》、《兵马俑为谁守护》轮番地上映,加上全国报刊杂志以及各种网站几百万次的转载和传播,“芈月”两个字,已经变成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事情了。
《芈月传》跨年度热播,让蒋胜男火了一把、让导演郑晓龙火了一把,让最先提出宣太后名字叫“芈月”的陈景元,随后也火了一把。应该说,世界真是无奇不有,他们不约而同走到一起:没有陈景元对芈月的研究,不会引出蒋胜男的小说;没有蒋胜男的小说,郑晓龙就不会成功拍摄这部电视剧;没有郑晓龙的大片,“芈月是兵马俑主人”的影响力,就不可能达到世界的每个角落,人们也不会知道“芈月”两个字,是陈景元历经四十多年艰苦磨练,才修得的正果。
《芈月传》播出之后,原来坚持“兵马俑主人是秦始皇”的人,立即进行了最激烈、最顽强的抵制:作家萧盛愤怒谴责说,将宣太后的名字叫“芈月”是对历史的无情奸污,而其罪魁祸首就是陈景元;著名考古学家段清段,更以“人咬狗才能变成新闻”的歹毒语言,对陈景元进行人身攻击;西北大学教授徐卫民,声称“对陈景元无聊的观点,没有兴趣进行反驳”,自己却跑到陕西省图书馆、西安博物院举办讲座,高呼“宣太后葬在秦东陵,芈月不是兵马俑的主人。”
与此同时,西安一些考古权威向记者发表高见,声称自己观点的牢不可破、不可战胜,却一直不肯对当年争论的症结问题,写出自己各种有针对性的反驳文章,让公众看看自己的论证材料,有多么的确凿、可靠和令人信服。除了嚣张的气焰不衰,毒舌腔调不改之外,始终说不出多少真正有份量的话。相反陈景元是将咒骂自己的话,变成动力,并将自己对“芈月”两字进行考证的详细过程,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,请公众本着公正、客观的原则,前来进行分析和检验。
1976年一位叫郑洪春的考古学家,在西安碑林得知陈景元对阿房宫有新奇观点时,就写了一个条子,让陈景元到西安市文管会找李家翰和姜开任,李姜两人见到陈景元的《阿房新谱》,十分高兴地说:“学建筑的人系统研究阿房宫,你是第一个,我们发掘阿房宫北司遗址时,发现有麻点纹的筒瓦,说明阿房宫不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。不过希望你能够帮来我们辨认一个字:北司遗址的筒瓦上有个很奇怪的字,请教过西安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,结果谁都说不认识。”
他们让陈景元辨认陶文,陈也说不认识,于是在本子上将笔划描下来,文管会开了一张去阿房宫公社的介绍信,让客人到发现筒瓦的高窑村考察一番。陈景元回到南京,一天去南京图书馆看书,碰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段熙仲教授,陈景元拿着怪僻字向他请教。段先生说:“中国古文字很有趣,经常有多一笔、少一笔的现象,有时减一笔,加一笔,就能把字认出来。这个陶文,其实是两个字,右边是月字,左边的字,将头顶的一竖,移下来,就是一个‘芈’字。”
阿房宫“北司遗址”发掘中,知道筒瓦上有个不认识的字,除西安市文管会李家翰、姜开任外,还有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高明教授。陈景元将这个陶文认定为“芈月”两个字,除了向中央作了反映之外,也已撰写到已经正式出版的《秦俑风波》一书中,外界如果对这个陶文有兴趣,可以与西安市文管会去直接联系,可以将筒瓦从库房中提出,看看它是不是如段老说的“芈月”两个字。姜开任不在了,李家翰已经86高龄,但是头脑非常清晰, 他们是筒瓦文字的见证者。
考古界很讲究论资排辈,他们的言论是否具有权威性,取决于他们在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,有人资历辈份都很高,但说话总是没人听。比如,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说“安阳墓”不是曹操墓,竟然一点用处都没有,姜开任被称为是考古泰斗,李家翰与徐苹芳、高明、俞伟超一样,都是1951年北京大学的同窗,个个都是顶级学术权威,他们决不讲假话、不做违心事。所以李家翰、姜开任对于“北司遗址”筒瓦文字的描述,是真实、可靠的,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。
由于阿房宫遗址有“芈月”陶文和“歪髻、偏髻”玉人的出土,以及有大量文献资料记载作为依据,使宣太后芈月是“阿房宫主人”的结论,已经变成板上钉钉的、不可推翻的铁案了,它厘清、还原几千年来一直被模糊起来的那一段历史,彰显了秦宣太后不为人知的重大功绩,肯定她是一位中国不可多得的、有杰出成就的女权人物,这是一件多么值得人们肯定、宣扬的大事情。这里要向人们进一步地证明,地处骊山北麓那个“世界奇观”,也是宣太后的一个杰作。
对于这个惊人的结论,很多学者是不愿意面对的。因为认可它就会引起学术大地震。比如,自己一旦认可秦宣太后的名字叫做“芈月”,认可梳着“歪髻、偏髻”是芈姓楚人传统的习俗,认可“阿房宫的主人”就是秦宣太后,立刻就会引起一个无可挽回的学术大坍塌。这是因为,在八十多里之外的骊山北麓西杨村附近,有几千个陶人也梳着“歪髻、偏髻”,陶人身上也有“芈月”的刻文,两个地方有着这么多惊人的相似,难道还不说明它们与宣太后直接有关吗?
秦俑考古队在1975年第11期的《文物》杂志上,发表了《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》,它首先公布俑坑的一个陶俑身上,发现有一个奇特的陶文,他们匆忙就说它是一个“脾”字,并且认为只是一个普通工匠的名字,断定这个字根本不可能具有其它特别的含义。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说它一定就是“脾”字,那是没有进行任何的论证和解释的,这个陶文不是现代印刷体,而是古代的籀文,显然他们是将陶文中除了“月”字的偏旁外,一定认为另一半就是一个“卑”字了。
但是细心的人们一定会发现,对于陶俑身上左半边“月”字的判读,是不会有任何异见的,而要将陶文右半边那个字,判读为“卑”字,就有很大问题了。因为“卑”这个字,无论在古代、或者现代,都是一个很普通、很常见的字,人们对它的字形、写法和读音,都是非常熟悉的,根本不用借助于各种字典,一下字就能够将它辨认出来。它如果确实是一个“卑”字,几乎人人都不会认错;它如果确实不是一个“卑”字,那么谁要说它一定就是,恐怕也是不行的。
真正的“卑”字,应该是怎样书写呢?这个“卑”字的写法,人们是司空见惯的,“卑”字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。如果将所有与“卑”字有关的字、或者将“卑”字各种写法汇集一起,人们一定会发现:从容庚《全金文》一书收录的古文字看,“卑”字有五种不同的写法;从徐文镜《古籀汇编》一书收录的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字形来看,“卑”字也有九种不同的写法。也可以说,“卑”字的形象,上部全都是一个圆圆的头,下部则全都有一条细长细长的小腿。
其实,在《中文大辞典》里收录的“卑”字,就更多、更直观、更能说明了。它里面显示的古文字材料,它的来源不仅有《说文解字》,还有著名书法家史游、孙虎经、王羲之等人六种关于“卑”字的写法。经过认真对照得出的结论是:所有这些古文字的经典写法,与秦俑坑陶俑身上的陶文,竟然没有任何一点的相同、或者类似之处。真不知道袁仲一等人当初除了臆断想象之外,还有什么可靠的依据,将陶俑身上这一个陶文,与“卑”字、“脾”字直接挂上钩的?
陶俑身上的怪僻字,袁仲一认定为是“脾”字,是没有一点点道理的,那么这一个怪僻字,到底是一个什么字?陶俑身上的怪僻字,说它包含一个“月”字,可信度是很高的,如果说怪僻字外一半有问题,无非是指那个“卑”字被否定之后,要有一个字去替代它。应该说这是学术之争出现一个的焦点和核心。而在“卑”字必须退出,人们要重新判读另一半的字形和字义时,南京的段熙仲教授原来提出来的“芈、月”一说,自然而然就要引起人们特别的特别关注了。
在遗留至今的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古文字字形中,“芈”单独出现的机率是很低的。人们要想找“芈”字原始的写法,要想与俑坑陶俑身上的陶文对号入座,而找出它的原始出处,估计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不管怎么样,它终究是古文字中曾经存在的一员,总是在历史上曾经单独存在的一个字。也就是说,虽然在众多独体字中,找不到它存在的可靠字形,那么人们在众多合体字中,能不能找到它的形象和痕迹呢?通过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,终于将它一个个都找到了。
从汉字的字库里,找到“畢、篳、華、崋、澕、樺、燁、曄、驊、鏵”这些标准汉字,实际上这些汉字,都由几个独体字组成的合体字,除了字的头顶有个“帽子”之外,它的下方都有一个标准的“芈”字。人们回头看看,这一些的“芈”字古文字与俑坑那个陶文的形象,就己经非常地接近了。即使在当代出版的《史记》之中,“芈”字也有五种不同的写法,所以将众多的“芈”字,从各种合体字分离出来进行辨认,应该是非常合乎情理、也是一种最正确的选择。
所有古文字资料,全都展示在世人的面前,人们完全可以确认俑坑的那个所谓的“脾”字,肯定就是段熙仲认定的“芈、月”两个字,应该认为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,更是一个不可以被任何人逆转的事情了,从单纯的学术论证角度上去看,争论的最后结论应该是有眉目了,这项研究也应该划上一个句号了。而让人不可理解的是,就在这一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,袁仲一等考古学家们,本来也应该就此止步,应该去面对现实,并且应该去调整自己以往的那种思路了。
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,有种种的迹象表明了,一场新的学术争论,又被他们逐渐地推到争鸣的讲坛上来了,袁仲一和他的许多支持者,仍然做出超常的反应。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,向自己的学术对立面,提出了一个新的反驳意见。他们坚持说:“陶俑身上的陶文,是一个字不是两个字,一个完整的陶文,一个完整的字,怎么能够采取拆开辨认,把俑坑一个好端端的陶文,竟然被割裂开来变成了‘月、芈’的两个字,这样一种做法,是严重违背古文字释字常规的。 ”
袁仲一对于陶俑身上那一个陶文,到底是不是“芈、月”两个字,已经闭口不谈了,他最新的观点是:“人们在释读古文时,必须忠实于原有字形,不能把一个完整的陶文,采取拆字的方法进行辨认。”人们应该如何回答他新的挑战?首先他对于汉字为什么不能进行拆分的问题,并没有拿出多少有说服力的理由来。人们应该知道,将一个完整的文字拆开来,字义可能有所不同,但是谁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一个完整的字,本身是可以由多个独体字构成的这个造字法则。
汉字发明和使用,是一件非常奇特有趣的事情,几乎在每一个朝代,都能够造出很多的新字来,所以汉字的数量实在是多得非常惊人的。比如,在《康熙字典》中,有47000多个字;在《中华大字典》中,有48000多个字;在《中文大辞典》中有56000多个字;在《中华字海》中有85568个字;在北京国安资讯设备公司的《汉字字库》中有91251个字?据统计,自公元前2098年的炎黄时期开始,一直到2012年的现代,估计出现过的汉字的总数量,已经超过了l0万多个。
汉字数量浩大,但最常用的汉字,仅仅只有3500多个,汉字的造字方式和结构,也是千奇百怪、变化无穷的。比如:两个“人”字,能组成一个“从”字,而三个“人”字,能组成一个“众”字。两个“日”字,就能组成一个“昌”字,而三个“日”字,能组成一个“晶”字。在现实生活之中,谁又能否认有的汉字,是由上下两个独体字组成,谁又能否认有的汉字,是由左、右两个独体字组成的,谁又能否认有的汉字,是由三个、四个、甚至更多独体字组成的。
在中国有许多古怪的文字,绝是大多数的人,既读不出它的音,也不知道它的含义。比如:两个“又”字,一般都认识它是“双”字,但是由三个“又”字和四个“又”字,组成的“叒”字和“叕”字,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字了? 如果再将两个“田”字,三个“田”字,四个“田”字叠在一起;又人们将两个“鱼”字,三个“鱼”字,四个“鱼”字叠加起来,又将两个“龙”字,三个“龙”字,甚至四个“龙”字捆在一起,人们就很难认出它们都是一些什么字了。
或许人们还记得:民间经常将“招、财、进、宝”和“黄、金、万、两”这些字,拼叠成了一个吉祥字。在陕西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之中,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小吃店家,在大门口高高地挂着一个奇怪的金色大字,虽然谁也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字,但是当地的大人小孩,一口气就唱出它的意思来:“一点飞上天,黄河的两边弯;八字大张口,言字往里走,左一扭,右一扭;西一长,东一长,中间加个马大王;心字底,月字旁,留个勾搭挂麻糖;推了车车,走咸阳。”
在现实的生活中,有许多的文字,人们确实是很难认识的,但是碰到了又不能回避,不能不去面对,所以聪明的人,往往就会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,将它们形容出来、比划出来。也就是说,人们可以将一个不认识的字、笔划很多的字,拆开分解成为好几个字,来进行辨认、来进行书写,总之难不倒任何人,会用各种方法,将自己碰到的怪僻字,逐一地将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,保存下来,也可以对这些材料,不断地进行琢磨,最后或许真的就能够揭开很多的秘密来。
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,常用“弓长张、立早章、古月胡、口天吴、木子李、人可何、言午许、木易杨”等口头语,可以形象地表述汉字的基本结构。“张”字,可以拆成“弓”和“长”;“章”字,可以拆成“立”和“早”;“胡”字,可以拆成“古”和“月”;“吴”字,可以拆成“口”和“天”;“李”字,也可以拆成“木”和“子”;“何”字,可以拆成“人”和“可”;“许”字,当然可以拆成“言”和“午”。汉字这种分分合合,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在同样的情况下,谁又敢断言很多怪僻字,只是一个独体字,而不是一个合体字?谁又敢说很多怪僻字,是不能够拆开进行辨认的?谁又敢说秦俑身上这个怪僻字,不是由“月、芈”两个独体字组合而的?人们不禁要问:即使袁仲一等人将陶俑身上这个怪僻字,释读为“脾”字,难道这一个“脾”字,不是合体字,而是独体字?不正是自己先将它拆成“月、卑”两字,再去做各种文章的吗?由此可见,袁仲一提出汉字不能拆分的观点和主张,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。
人们应该怎样对待独体字和合体字的问题呢?所谓独体字是指一个汉字,只有一个单独的形体,而不是由两个、或者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。独体字大都是一些简单象形字和表意字。这一类字,是从图画演变而成的,每个字是一个整体。如日、月、山、水、牛、羊、犬、戈、矢等,都是独体的象形字;又如天,立,上、下、一、二、三、见、门等,都是独体的表意字。这种独体字,是不能将再进行拆分,而成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,拆了就不成为一个完整的字了。
实际上,独体字在现在使用的汉字里面,所占比例是很小的。绝大多数的汉字,都是由两个、或者两个以上的独体字组成的合体字,而独体字才是众多合体字构成的基础要素,从这一个意义上看,就使得独体字一直成为了汉字结构系统的主体和核心。就秦俑身上的这个怪僻字而言,它到底是独体字,还是合体字,如果是独体字,是不可以拆分的;如果是合体字,是可以拆分的。所以将合体字作为一个切入点,去判断这个怪体字的字义,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用合体字的方法,去认定俑坑这个怪僻字,到底合适不合适、到底可取不可取呢?秦俑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,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。他在1984年9月撰写的一篇题为《近年秦俑研究述评》的论文中,明确无误指出:“陈景元提出了铁兵器的问题,以及对陶俑的陶文,重新释读为“芈”字,这无疑是正确的。”人们都看到了吧,秦俑馆本来承认,陶俑身上的那个陶文,陈景元将它由原来认定的“脾”字,重新释读为“月、芈”这样两个字,应该是没有一点点问题的。
也就是说,包括袁仲一在内的其他秦俑馆考古学家,如果还要坚持陶俑身上那个陶文,仍然只能是“脾”字的观点,那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了。在这里也要奉劝袁仲一几句话,对于陶俑身上这一个怪僻字,首先要下一点功夫去核对和认真地探讨一下,对于那个陶文,到底是不是真正像传统意义上的“卑”字,还是像各种古文字资料中频繁出现的“芈”字,请先在秦俑馆内部,认真探讨一番,争论一番,等到统一意见后,再对外公开发表,似乎会好一点,稳妥一点。
在学术冲击波的强烈撼动之下,袁仲一等人可能也发现,自己对于“脾”字的错误判读,是太明显了,存在的学术漏洞,实在也是太大了。但是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“芈、月”就是秦宣太后的名字,恐怕在感情上还是很难通得过的。袁仲一在1985年发表的《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》这篇文章之中,提出以下一个全新的观点。文章说:“退一步说,那个陶文即便是芈、月两字,也是与秦宣太后毫无关系。因为俑坑中出土大量陶文,都是俑的编号、或者陶工名。”
在袁仲一看来,陶俑身上的文字,即使真的是“芈月”两个字,也与秦宣太后无关,但是只要有谁能够证明“芈月”不是陶俑制作工匠的名字,那么“芈月”两字的存在,他也许就不再坚持原有否定的态度了。在这里,一定要请他记住自己说过的这一番话,如果陈景元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,能够运用充分、可靠的材料,去否定“芈、月”这两个字,确实与塑造陶俑的工匠毫无关系的话,那么就要请袁仲一等人,痛痛快快地去承认芈月就秦宣太后名字的这个结论吧。
人们从《秦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》一书中提供的数据来看,在一号坑中出土的陶俑数量是1087件,而在陶俑身上有陶文的俑,也仅仅只有382件,有字的陶俑只占35%左右,其它大部分的陶俑,身上都是没有任何陶文的。另外,在382件有字的陶俑中,只有62件是印文,其余的都是刻文。这些现象到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?首先如果“物勒工名”落到实处的话,既然制作的陶俑都要编号,那么就应该做到一个陶俑一个号,1087件陶俑,完全应该有1087个编号。
大部分陶俑没有编号,说明制作陶俑时间,是在吕不韦担任宰相之前。请人们注意,秦国“物勒工名”,是吕不韦提出并且付诸实施的。这里必须调一下,陶俑身上刻的数字,与工匠塑造工作量毫无关系。这是因为,在382个陶文中,带有数字符号的只有190个,但不能说它们是陶俑的编号。在陶俑身上刻“一”的有3个;刻“二”的有14个;刻“三”的有5个;刻“四”的有20个;刻“五”的有32个;刻“六”的有13个;刻“七”的有10个;刻“十”的也有20个。
190个陶俑中,有32个同时以“十”编号,有20个陶俑同时以“四”编号,这难道真的是给陶俑编号的?袁仲一难道不应该将陶俑,有的有号、有的没有号,有的号闲置没有用,有的号竟然同时用了30多次,对这种奇怪现象,进行一番必要解释吗?有一点是完全肯定的:人们有理由相信,在日常事务中,凡是要以编号进行统计,不会出现一个号,同时多次使用的,陶俑身上连号都编得如此无章无法、杂乱不堪,这与秦始皇时期实行四级管理制度完全是背道而驰的。
袁仲一提出陶俑身上陶文只是工匠名字的观点,就更站不住脚了。不知人们有没有注意,如果要说陶俑身上的陶文,一定是工匠名字的话,那么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更多更严重了。这是因为;制作陶俑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,制作陶俑的工序也很多,环节也很多,决不是单靠一个工匠,就能够顺利完成的。比如:制坯、造型、干燥、烧窑、彩绘、拼装,参加的工匠人数也数不清,如果在陶俑身上都要刻上名字,就要刻一大片,不然出了质量问题,谁都负不了这个责任。
还有陶俑制作,采用的是大批量的模制方法,有的人大量制作手臂,有的人大量制作俑头,有的人大量制作身躯,等到各种半成品一批一批制作完毕,最后再进行总体的安装,这时制作陶俑躯干、手臂、头部的工匠,都是很不相同的,如果工匠都要去刻名,那是没有办法刻、没有地方刻的。在382个陶文之中,有62个是印文,其余的都是刻文,这说明了62个印文,是在泥坯还没有干透前,就印到上面去的,而其它刻文,都是在陶俑烧制完成之后,才匆忙刻上去的。
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陶俑身上的陶文,人想刻什么就刻什么,根本没有规律性可言。实际的情况是,由于陶俑都是出自众多工匠们的手,一开始只是制作泥坯,接着塑造陶俑形象,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惹事生非,去乱刻乱划的;有少数人,在不起眼的部位,拿工具去划上几条线,刻几个名,都是有可能的。甚至将所恨的人,刻在上面,发泄一下,也有可能。过去人们在乡间大树上、石板上、甚至在厕所里,经常看到打倒“谁谁谁”的字,其性质应该都是一样的。
陶俑身上,还有“咸阳、安邑、临晋、栎阳”等字,这是典型的地名,而与工匠名字无关。在陶俑身上,还有“不、少、宫、咸衣”等与工匠名字不相干的字。另外,有五个陶俑的颈部,都刻“冉”字,而在秦国的历史上。以“冉”为名的人,只有一个,那就是秦国早年的宰相、秦宣太后的弟弟魏冉。袁仲一凭什么一口就咬定除了一些奇怪的数字以外,凡是有字的,也包括那一个怪僻字,除了猜想还是猜想,根本没有任何理由,说它们都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字。
2016年1月考古学家在湖北棗阳郭家发掘现场找到一件春秋早期的青铜鼎,在这一个鼎上,赫然醒目地显现一个清晰的“芈”字。据湖北省考古所所长方勤先生介绍说:铜鼎上刻有“曾侯作季汤芈鼎”的铭文。当然,铜鼎上的那一个字,实际上也是一个合体字,它是由一个“芈”字和一个像“弥”的字,所共同组成的,而其中的那个“芈”字,当然也是一个独体字。青铜鼎是春秋时期的,陶俑是战国时期的,由于两者相隔几百年,所以书写起来还是有少许差别的。
到此,以上就是小编对于被卖掉古石碑已追回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,希望介绍关于被卖掉古石碑已追回的1点解答对大家有用。
-

国足vs卡塔尔-=-国足vS卡塔尔时间?
大家好,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,就是关于国足vs卡塔尔的...
-

2014足协杯决赛绝杀视频最新-=-2014足协杯决赛完整视频
大家好,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,就是关于2014足协杯决...
-

安踏中国国家队-=-安踏中国国家队队服
大家好,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,就是关于安踏中国国家队的...
-

湖人vs魔术总决赛录像2-=-湖人vs魔术总决赛录像2022年
大家好,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,就是关于湖人vs魔术总决...
-

fivb比分直播-=-flfa比分网
大家好,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,就是关于fivb比分直播...